查合倫昭慶打量面前的年輕男女。其中的女性已經不陌生,是被死去的久慶選中的蘇硯君。男子雖然是第一次拜見,但他陳景初的大名早已同他父親的名字一起,在昭慶的耳邊響過若干次。昭慶一臉不解,「為什麼蘇小姐會同來?」
陳景初不疾不徐地說:「蘇小姐有件事要向大人稟明。」昭慶的眉頭向上挑了挑,「我以為陳公子來,是要商量官民共保縣城,免遭妙高魔頭們的侵犯。」
硯君不知道他們之間還有要事,覺得有些尷尬。景初不動聲色地說:「防範那些魔頭行兇施暴,當然是當務之急。大人是一縣之長,需要陳某出力,只需一聲令下。蘇小姐這件事情,對她一家人來說也是刻不容緩。況且大人過問一下,用不了多少時間,我等著就是。」
他表態之後,昭慶刻板的面孔顯露出放鬆。他雖然是縣官,剛剛到任就要做好對付魔教攻城的準備,畢竟有些心虛。陳家在當地一言九鼎,只要開口,比縣官的號召力強得多。但昭慶的性格與久慶大不相同,他並不懂得昱民言語中的關竅,也不知道他們做事要求禮尚往來。他沒聽出景初要他先辦完蘇家的事情,才肯繼續商談。昭慶以楚狄赫人的直率,說:「妙高魔頭來犯,是全城人生死攸關的大事,蘇小姐事情再大,不過是她一家人的事。我想請陳公子一起,仔細商談動員城民防守的事情。今晚實在沒有多餘的時間。蘇小姐先請回,明日再來。」
景初見新來的查大人只取不予,心想此時談還好說,待到陳家幫完了忙,還能求得動他嗎?再要說話,卻聽見硯君說:「一家之事的確不能與一城之事相提並論。」景初忍不住蹙眉:這位小姐果然不諳世事,又犯傻了。同官場上的人談條件,互相漁利尚無十拿九穩的把握。自己先鳴金收兵,還要怎麼再轉回場上?
硯君朗朗地說:「我不是本地人,不及陳公子聲威顯赫。然而一日在此,便同此城休戚相關。但願妙高山人來犯只是一場虛驚。如若當真受困,大人保城需要差遣,我雖是女子,亦有綿薄之力,願為效勞。」
昭慶見她眉目透出澄朗之氣,暗道久慶的眼光還是不錯的,連聲道「好」,又說:「蘇小姐家中有何難事,明日我定秉公處理。」他不知道硯君家裡的事就是刺傷鹿知,匆匆將硯君請出門外,便拿出城防圖要景初動員民眾各處防守。
夜色已晚,下了整天的雪不知不覺停住。天地間充滿冷得無法流動的寒氣,硯君驟然從溫暖的室內走出,恍如沖入一個安靜的冰殼子。凍住呼吸的冷,讓她想起弟弟和金姨娘還在牢房中領略苦寒。自己又沒能幫上忙,他們今夜不得不結結實實地受罪。可她實在無法攔住查大人,要他別去商議民防、先放金舜英。
既無道理打斷查大人和景初的對話,又不能心安理得地回去休息……她微微低著頭,站在寒冷的曲廊,看著自己呵出的白氣發呆。一晃神,不知過去多久。
有人沿著曲廊走過來,起初沒注意到她,猛然發現時,提起燈籠舉到她面前。硯君被燈光晃了眼,「啊」的叫一聲,也驚了對方,搖滅了燈籠。他們互相提防著保持距離,不約而同地大聲喝問:「誰?!」
躲入雲層小憩的玉輪被叫聲驚醒,穿透重雲,照亮滿世界鋪陳的白雪。被雪與風擦淨的夜色,在他們周圍泛起了光。
鹿知看到一張皎潔的臉,令人想起凝固的月光,冷而清亮。他目不轉睛地看時,她的眼睛眨動,交睫的剎那,凍在睫毛上的的淚花細碎地閃爍。「七爺!」雪地上飄起了悅耳的驚呼。
鹿知收回神,板著臉「嗯」一聲,裝作沒有立刻認出她,上下打量之後說:「是你啊。」
硯君也「嗯」一聲,除此之外不知道怎麼回應。想起景初的僕人還在門房等著,她匆匆地說:「我該走了。」鹿知充滿狐疑的目光打量她,「這麼晚,你找昭慶做什麼?」
硯君忽想:他的來頭頗大,連查大人也要敬他,此時遇到他,莫不是天意?她可不能再錯過解救弟弟和金姨娘的機會。更多更快章節請到。她深深地施禮,惹得鹿知莫名其妙。
「其實是有一事,前來請求查大人開恩。大人為保城池憂心忡忡,民女不敢以私事耽擱。事壓心頭,六神無主。既然巧遇七爺,不知七爺肯否隨意聽聽?」
鹿知心想:你以為別
求情(2) 『加入書籤,方便閱讀』
 傲嬌星媽:調教男神當奶爸 艾淺淺撿了一隻受傷的男人回家了。某男不僅用她的,吃她的,住她的,最後竟然還脫得光溜溜的爬上了她的小床!艾淺淺小臉爆紅的咆哮,「季天騏,永遠有多遠,你
傲嬌星媽:調教男神當奶爸 艾淺淺撿了一隻受傷的男人回家了。某男不僅用她的,吃她的,住她的,最後竟然還脫得光溜溜的爬上了她的小床!艾淺淺小臉爆紅的咆哮,「季天騏,永遠有多遠,你
 夫人你馬甲又掉了 【腹黑慵懶巨有錢男主vs高嶺之花藏得深女主】秦苒,從小在鄉下長大,高三失蹤一年,休學一年。一年後,她被親生母親接到雲城一中借讀。母親說:你後爸是名門之後,你大哥自小就是天才,你妹妹是一中尖子生
夫人你馬甲又掉了 【腹黑慵懶巨有錢男主vs高嶺之花藏得深女主】秦苒,從小在鄉下長大,高三失蹤一年,休學一年。一年後,她被親生母親接到雲城一中借讀。母親說:你後爸是名門之後,你大哥自小就是天才,你妹妹是一中尖子生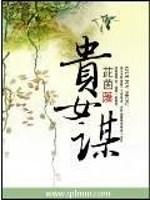 貴女謀 宅斗是可怕的蘇九一向知道,真正穿越了這才知道宅斗要素中的豬隊友狼對手都可以弱爆了,可怕的是披着羊皮的狼隊友,叼着血淋淋的肥肉硬要她吃下,再肥美的肉也是人肉啊!這怎麼破?
貴女謀 宅斗是可怕的蘇九一向知道,真正穿越了這才知道宅斗要素中的豬隊友狼對手都可以弱爆了,可怕的是披着羊皮的狼隊友,叼着血淋淋的肥肉硬要她吃下,再肥美的肉也是人肉啊!這怎麼破?